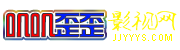Netflix最近上了一部以精神病患为题材的高分原创剧。名字挺温柔的:《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》(It’s Okay to Not Be Okay)。
时隔5年复出的金秀贤(钢太),这次在剧中扮演了一名在精神病院上班的护工。他邂逅了一名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童书作家,开启了一段“情感疗愈”之旅。

作为故事主要发生的场所之一,钢太上班的地方——没关系医院,也展现了部分精神病院内景。
比如,身边会有很多行为奇怪的病友。
对着空气说话、旁若无人的唱歌,或是觉得角落角落都是监控,正在监视ta:

他们可能没有行动上的自由。
病房是封闭的,窗户是锁死的。要是发起病来,可能还会被三五大汉架在床上,注射镇静剂。

病人不肯吃药。他们练习各种藏药绝技(比如假装把药拍进嘴巴,实际藏在指缝里),每天和医护斗智斗勇:

影视剧和小说为我们的提供了夸大想象的基石。
对于“精神病院”,普通人总是会存有很多想象,也有很多误解。许多人听到严重到要住院的“精神病”,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情况了。
真实的精神病院是什么样?
其实,简单心理的很多心理咨询师出于工作需要,都曾在精神病院呆过一段时间。
我们联系了林荫、岳也、周正朗,跟她们聊了聊咨询师眼中真实的精神病院生活。
涉及病人隐私之处,均做了模糊处理。

去精神病院这件事,对我来说就像是“田野调查”。
我想知道一下自己不了解的那些东西。一个人怎么就成了那样子?书本上写的那些症状,如何在真人身上出现?说大一点,你可以在那里高密度地看到人类的苦难。
那段时间,精神病院就像“另一个世界的9又3/4车站”,我咔地冲过去,然后就到了一个魔法世界。
——林荫,2018年夏天,北京回龙观医院

说到精神病院,普通人可能想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符号。
去回龙观之前,我也听了很多传闻。比如你不能在空地站着,一定要背靠墙,保证前面有人过来是能看见的,防止病人突然冲过来。
但毕竟我学的是心理咨询。我对这些事感兴趣,加上时间充裕,所以开放病房、封闭病房我都去呆过。
精神专科医院病房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。开放病房的管理要宽松许多,病人的意识相对清醒,家人可以陪住,病人可以自由在病区内活动和使用手机、电脑,需要外出办事征得医生允许便可,与我们通常了解的综合医院病房基本差不多。

封闭病房,住的是重型精神病人。
在那里,每个病区有一道单独的大门,全天24小时锁门,工作人员进出病区要立刻上锁并二次检查。病区大门好像一道生死线,医护人员对病人靠近大门的意图或行为会格外敏感警惕,因为闯门的事情确实时有发生。
封闭病房的病人一般比较严重。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,确实是“好不正常”。
早上查房,会看到处在发作期的病人在那手舞足蹈,唱“一个小草”;还有人在旁边砸床,自己对着空气说话,大家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……有人20多岁起病,住到现在可能已经四五十岁了。
最初一周时,他们突然发作的场景会给我很大情感冲击。有时候病人无法自控,需要护工把他束在床上。
大家不想伤害到他,但是又怕自己被伤害到,你知道吗?那确实是一种“冲突”的场景,虽然他并没有跟谁对峙。
去男病房要更害怕一些,因为男病房都是大老爷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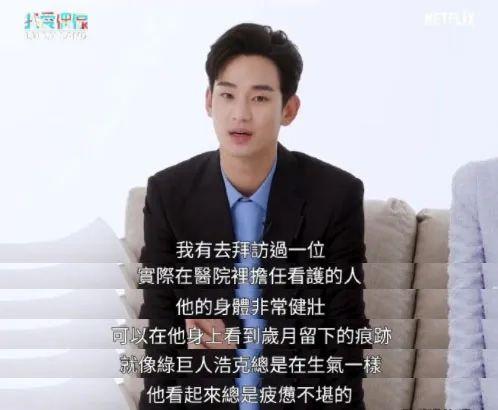
不过,跟病人熟悉了之后,什么人即将发作都有征兆。比如说话有点开始乱套了,嗷嗷地跑进跑出——他们就说“XX又不好了”。他们用的专业的词就是“不好”。
听着是挺吓人的,但医生就比较淡定。我后来呆久了,也淡定了。
除了发病的病人之外,我不会有多害怕他们。只要是意识清醒,然后能正常说话的,我都可以聊一聊。
其实也就是很普通的聊天。听听他们那些喜怒哀乐,或者吐槽一下父母之类的。哪怕他感觉此刻好了一点,也很有价值。

我刚到病区时,曾经很楞的问过医生“用什么标准判断要不要把病人捆起来”,当即被医生严厉批评说“注意你的用词。这不是捆,而是保护”。
我作为心理咨询师,觉得挺难受、也挺难以处理的一个部分,是患者在病房里那种孤独的状态。
你看现在这个时代了,也不能让他们把手机带进去。一个病房里60个病人,只有1个公共电话,每天中午轮流排队打,每个人只能打三分钟。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单调枯燥、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关系、陪伴对康复是很重要的因素。但在封闭病房的环境下,这是两难的事情。
有时候,精神病真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绝症”,就是一种生活的绝望感觉。他们可能会反复发作,带病生活。
说一句庄严的话,人最宝贵的就是相信有希望。在困境面前,你通过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来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,Possibility这个词太美丽了。没有可能性,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审判。

去精神病院的病人,其实已经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了。对于处在发作期的病人,心理咨询很难有什么实际帮助。
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最开始告知我们:这是个见习,不是实习,不是要求你来做些什么,你也做不了些什么,定位非常明确。我觉得这对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是一个很大的保护。
——岳也,2012年夏天,北京安定医院
去精神病院见习,是北大心理系研究生的受训项目。2012年暑假,我刚刚读完研一,就和其他3个同学一起,像个小分队一样去了安定医院。
8年前,我觉得精神病院人好多,床位也很有限。
安定没有回龙观那么大,环境也比较老式,是那种绿色的墙和铁门。医院里按照不同的严重程度和诊断分了十几个病房,一些社会功能好的病房不封闭,一些是封闭(也就是进出上锁)的。

在病区印象很深的患者,是个有性创伤的年轻女性。
她总是讲很多鬼怪故事,告诉我们魔鬼昨天又对她做了什么,“我被魔鬼控制了、我被魔鬼侵犯了”!还有非常多的强迫症状。
我当时很被触动的是,她遭遇过事实上的性侵和家暴,包括父母的早期分离。
她的语言体系虽然难以理解,但你会发现,那些奇怪的语言表达跟情感状态是匹配的。那样的病人,通常是因为经过非常深的创伤,让生活太难以承受和维持了。

在整个见习期间,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的,是医生的快速诊断能力。
跟患者聊天的时候,医生会进入到他们的故事里,使用他们所用的语言。比如问一个妄想的病人:“你昨晚又见到了谁”?问的时候好像云淡风轻,问题都非常简单,但他们可以马上从中评估出病人的状态。
还有他们对待病人的方式。
好多年前,有个青春期的躁狂症病人,她喜欢上一个特别帅的医生,然后会对医生有很多性的表达,比如直接过去要抱医生之类。她这个行为,其实会被很多其他的病人取笑。
我记得当时医生是抓住了她的双手,没有让她真的抱上来,比较温柔拒绝了她,没有羞辱的那种感觉。对,又温柔又有边界,然后使用病人的语言跟她回应。我会记得那种感受,是特别温柔的。

病人的表现真是丰富多彩。他们跟一般的来访有区别,但不会像我之前想的那样好像一个鸿沟、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那种区别。不是,他们有点像一个连续谱,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连续谱。
从这个角度看,当他们出现症状的时候,只不过是离正态分布偏离了一点点。我觉得人的复杂性这件事情,真不是你的标准能够概括。
——周正朗,2018年夏天,北京回龙观医院
我是自己跟医院约的见习。因为在成为咨询师的过程中,其实有一些困惑。
当时我还是很新的新手,会接到一些来访者有精神科诊断。所以我好奇,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得到一个诊断?他们在精神病院会受到什么待遇?虽然我所接受的培训会提到这一块,但是教的很理论。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回龙观医院。他们有个院子,感觉特别老派,有那种80年代的老单位的感觉。
刚一进去,其实气氛特别祥和。一个小花圃,然后旁边是有点老式的楼。有一些病房是封闭的,病人只能在固定时间出来活动,三三两两的。

我去的是开放病房,接触的是成人和青少年的神经症病人。如果不是穿着病服的话,他们看上去其实和普通人差不多。
我对一个有躁郁症的孩子印象很深。她长得好看,有点像《隐秘的角落》里的普普。有天早上她突然情绪崩溃,说想要出院,然后疯狂地哭。
可能是因为咨询师接的来访,一般都呈现出社会功能比较好的样子。跟他们的交流,会随着一对一的探索,慢慢呈现出情感的流露。那不是一个很突然的过程。
而那个小女孩的崩溃是突然的,没有任何征兆(可能是因为我对她没有深入了解)。跟平常热情开朗、呼朋引伴的样子反差也实在很大。

另外,虽然医生对于病人都有一些职业化的套路,但其实都是关心的。
有的时候,医生看起来很冷漠,脸一板挺冷酷的,但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,才需要有一点冷漠的感觉。
早上门诊量很大,病人情绪强度也大,许多人滔滔不绝。如果卷入的太多,对医生来讲是非常耗竭的事情。
病人能够感觉到大夫的善意。一些病人因为住的时间长,家属、病人、医生之间互相都很熟悉,经常会进行谈话、沟通。虽然不算是非常严格的治疗,但会觉得他们的家庭结构里面的那些压力,有了一个往外宣泄的出口。

我之前对有诊断的来访有顾虑。因为有些来访的抑郁症状非常明显,他已经丧失对话的意愿,沉浸在情绪里头重复说一些螺旋话,甚至有轻生念头。
这些人可能会循环地发病,如果没有进行任何药物控制的话,每一次都可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。纯靠咨询师来打捞,压力非常大。
但去了医院以后就没有这种感觉。他们跟一般的来访有区别,但不是好像一个鸿沟一样,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那种区别。
药物可以从化学的角度帮到他,让他更容易从谈话治疗中获益。

“无力感”、“有限性”。每个受访的咨询师都提到了这些方面。
心理咨询常说,要转化创伤、转化苦难。“但心理咨询的来访者常常是相对正常、有起码的社会功能的。在人际和人格上一些问题,我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转化。但精神病院里的这些长期、严重的苦难,你会觉得好难转化,这些苦难就像一座山。”林荫说。
她觉得,对精神病人由来已久的“污名化”,也是一种对“无力”的反应。人们害怕自己掉到界限的那边,所以要强调我跟他们不一样,作出二元对立的一种防御性反应。
陶勇医生最近有一段采访很出名。他说:

“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站在今天的一个衣食无忧、生活安定、有稳定生活保证的情况下,我们去评判别人是好是坏。而事实上我也经常问自己,如果有一天我也穷困潦倒,到了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时候,我会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吗?我觉得好像我也未必做到。”